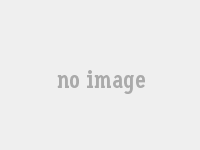东西方文化论战,贯穿新文化运动始终,是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921 年,新文化运动修成的又一正果,就是在这一年,人们收获了对东西文化重新进行审视的三颗硕果,三部代表性甚至可以称作经典性的著作。这就是这部《典藏1921》所收录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清代学术概论》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为什么说这三部著作是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东西方文化论战的三颗硕果?这里,对这三部作品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和评价。
第一颗硕果是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


蒋方震,字百里,以军事家著称。1905 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毕业。1906 年,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旋被公派德国研习军事。1910 年,返回北京,为京都禁卫军管带。1911 年初,回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担任原职。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陆军部高等顾问、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军事参议。1912 年年底,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6 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入川辅佐蔡锷讨袁。1917 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1925年后,曾经程度不等地辅佐过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1935年,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1938 年10 月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
在同时代军人中,蒋方震可能又是一位最具文人或学者气质者。1901 年,他东渡日本留学。1903 年2 月,参与创办《浙江潮》,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期间结识梁启超,执弟子礼。1918 年至1919 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成为新文化运动自具特色的一翼。1920 年9 月,梁启超与蔡元培、汪大燮等人发起成立讲学社,蒋方震出任讲学社总干事,负责接待英国哲学家罗素、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并担任研究系最有影响的刊物《改造》杂志的主编。1921 年,他与郑振铎、茅盾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3 年,还与胡适等人一起创办新月社。所以,对于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其中各派的观点,他有相当敏锐和深度的了解。他所撰写的这部《欧洲文艺复兴史》,正是试图对新文化运动中常常争论不休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回答。
这部《欧洲文艺复兴史》的撰写,直接缘于蒋方震和梁启超等人结伴欧游。1918 年11 月梁启超决定以私人资格去欧洲做一次详细的考察,他争取到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会外顾问的资格,由大总统徐世昌提供6 万经费,又从朋友处募集了4 万。陪同梁启超赴欧的,有蒋方震、张君劢、徐新六、丁文江等人。他们以巴黎为大本营,从1918 年12 月底到1920 年3 月,用一年多时间考察了英、法、德、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瑞士等主要欧洲国家,会见各国政治家、外交家、社会名流,拜访过柏格森、倭伊铿等著名学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社会经济萧条、物资匮乏、政治动荡的严峻现实,使梁启超深受刺激,撰成《欧游心影录》,记述了他在欧洲所见所闻以及他心路变迁的历程。他看到西方文化的进化论、功利主义、强权崇拜导致欧洲军国主义思潮泛滥;近代以来,科学在西方世界日渐昌明,创造了丰富无比的物质财富,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以为科学无所不能。科学取代了其他的一切思想、学说,尤其是哲学和宗教。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这一“科学万能之梦”。梁启超写道:“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功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到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梁启超反过来重新观察中国文化,认为西方文明总把理想与实际分为两样,唯心唯物,各走极端,科学与宗教信仰也如同水火,而中国文化则“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如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是“出世法和现世法并行不悖”。他认为,中国文化的这种取向,有助于西方文明的自我调适。因此,他向中国青年一代大声疾呼:“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蒋方震在陪梁启超考察战后欧洲时,对西欧文艺复兴留下的成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法国,蒋方震、梁启超等请巴黎大学图书馆主任给他们讲述西欧文艺复兴史,蒋方震还做了笔记。梁启超说,他们一行欧游中,蒋方震常昌言于同伴:“吾此行将求曙光。”他人时常戏问他:“曙光已得乎?” 他总十分认真地回答:“未也。”如是者数四。及将归,复有诘者,蒋方震一本正经地答道:“得之矣。”至于所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曙光,他则未尝言明。
佛家有云:“疑乃觉悟之机。小疑则小悟, 大疑则大悟, 不疑则不悟。”蒋方震是带着“大疑”而去,经过实地仔细考察和苦苦追寻、思考和研究,终获“大悟”。他所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欧洲这两三百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文化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他发现,不了解欧洲的文艺复兴历史,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在这一点上,他和梁启超旨趣很不一样。
回国以后,蒋方震就开始着手撰写《欧洲文艺复兴史》。他从欧洲带回一批相关书籍,又在国内努力搜集各种文字的有关资料。1920 年7 月2 日,他写信给梁启超说:“文艺复兴已成一半,搜集材料甚苦,近得德文书数种,大有助,先生处有日文佛兰西文学史( 玄黄社发行者已有),恳检数种寄下。”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使这一部著作具有很强的学术性。
《欧洲文艺复兴史》首为导言,第一章为总论,第二、三章为伊大利之文艺复兴(上、下),第四、五章为法国之文艺复兴(上、下),第六章为北欧之文艺复兴:弗兰特、日耳曼、英吉利,第七、八章为宗教改革(上、下),新教之流布及旧教之改良,第九章为结论:文艺复兴之结束。
蒋方震在该书《导言》中指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类精神界的一声春雷,它直接产生了以下两大结果: 一是人的发现,二是世界的发现。
所谓人的发现,就是人类自觉。在欧洲中世纪神权时代,人与世界之间,间之以神; 而人与神之间,又间之以教会。文艺复兴,使人与世界直接交涉。宗教改革,使人与神直接进行交往。人,并非神之罪人,尤非教会之奴隶。人有耳目,不能绝聪明; 人有头脑,不能绝思想; 人有良心,不能绝判断。这就是以人文主义打破神权主义。蒋方震所看到的曙光,首先就是文艺复兴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以人性代替了神性,以世间的财富、艺术,爱情、享受代替了禁欲主义,让人们相信人自身的创造力,而不再祈求神赐予力量。
所谓世界的发现,就是不再像中世纪教会那样以现世之快乐为魔,而能够直面自然世界,将大自然作为人所研究的对象。中古宗教教义,以地球为中心,凡有不同的见解,就斥为异端邪说。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些世界之奇迹,启发人们的好奇心,使得旧教义之蔽智塞聪者,无以自存。
蒋方震认为,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的但丁(1265-1321)为开山祖,而以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 集其大成,成为西洋文学的最高峰。文艺复兴,其根本精神实发生于个性之自由,其最高潮为法国大革命。
蒋方震同时指出,文艺复兴之弊,即为现世享乐物质,个人主义大盛,而怪僻、骄奢、残忍、阴险等恶德相随而来。
蒋方震特别强调指出,研究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中国说来,具有特殊的必要性。这是因为“以中国今日之地位言,则社会蝉蜕之情状实与当时欧洲有无数共同之点”。他认为,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新理性借复古之潮流,而方向日见其开展”,二是旧社会妨碍个性发展的组织日见瓦解,人们发扬独立之精神,实与欧洲文艺复兴声气相求。“察往以知来,视人以律已,则可知文化运动之来源有所自,而现状纷纭之不可见且不足悲也。”
蒋方震的著作于1920 年12 月初完稿后,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欣然应允。蒋方震书中曾提到,清代汉学特别是经今文学的兴起和欧洲文艺复兴有相似之处,说“汉学以尊古相标榜,其末流则尊诸子于经传,而近世首发攻击旧学之矢者,实为导源于今文派。”这一论点激起梁启超极大兴趣,他就对蒋方震说:“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果尔,吾前清一代,亦庶类之。吾试言吾国之文艺复兴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蒋方震当然无异议。梁启超即本此意动笔,下笔竟不能自休,十五天时间写成洋洋五六万字,篇幅几乎与蒋方震的著作相当。梁启超自称,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另成一书,这就是《清代学术概论》,只得另外写了一篇序言,说明蒋方震撰写此书原委,高度评价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
1921 年,《欧洲文艺复兴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我国人士所撰写的第一本系统介绍欧洲文艺复兴历史的专门著作。该书出版后,极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一年多时间就印了三次。著名学者张其昀在六十多年以后,仍称赞《欧洲文艺复兴史》“网罗宏富,条理详密,断制谨严,至今尚未见其比者,这是非常令人感激与深刻怀念的。”
东西方文化论战1921 年的第二颗硕果,就是梁启超的这部《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原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完稿之后曾在《改造》杂志上连载,稍后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在此之前,论清代学术演变的著述已经不少。论嘉庆、道光之前学术者,有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以汉学为中心,勾勒清代经学师承,自阎若璩、胡渭开始,终于黄宗羲、顾炎武,共辑五十六家传记与学术思想,对汉学家中惠栋所代表的吴派,尤推崇备至。该书问世不久,方东树所撰《汉学商兑》,和江藩所著《汉学师承记》针锋相对,批评清代汉学家“其蔽益甚,其识益陋。其所挟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汩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要之,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极力维护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道光年间,又有唐鉴撰《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分列《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经学学案》《心宗学案》五个学案,共列清初至嘉庆间学者二百六十一人,各为之传,记其生平、学术渊源、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每传后附以同学或从游者、问答者。全书宗奉朱子之学为正学,凡不宗奉朱子者即定为非正学,对传道、翼道、守道、穷经诸儒极力表彰,门户之见丝毫不加掩饰。
对清代学术作全面回顾与概括者,是章太炎《訄书》中的《清儒》一文。章太炎认为,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等人考订音韵、辨伪古书,奠定了清代学术的规模,但直到乾嘉时期形成的吴、皖二派,清代学术才趋于成熟完善。吴派代表人物为惠栋,其学术特点是“好博而尊闻”。惠氏在其著作中广泛搜罗汉人经说,加以排比罗列,而很少发表己见。除六经外,还兼及史集,涉猎很广。惠栋的弟子有江声、余萧客等,著名学者王鸣盛、钱大昕也受其影响。皖派始于戴震,其学术特点是“综形名、任裁断”,实事求是,在训诂考证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观点。戴震在乡里时,即有金榜、程瑶田、凌延堪等人与其论学,后执教于京师时,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其问学。而弟子中最知名的有段玉裁、王念孙,二人的《说文》和《广雅》研究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除去吴、皖二派外,《清儒》还对浙东学派万斯大、万斯同兄弟以及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的史学,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的礼学,善治文辞而轻视经术的桐城派,以及常州今文学派作了分析和评价,认为常州今文学派宗《公羊春秋》、齐《诗》和伏生所传《今文尚书》,而以《公羊春秋》为主。他们立意奇特,文辞华丽,与朴学家质朴的学风迥然有异,而受到文士的欢迎。常州今文学始于与戴震同时的庄存与,后经刘逢禄、宋翔凤,至道光时魏源、龚自珍、邵懿辰,影响日广。章太炎评价经古文学家“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故对经今文学家以经术明治乱、以阴阳断人事多所非议,但大体而言,他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总览还是符合实际的。
《清代学术概论》其实并没有对清代所有这些学术流派作全面介绍与分析。他说:“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重点就在考证学与今文学这两大潮流如何形成与发展,所以,原定书名《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可能倒更为确切。
为和欧洲文艺复兴历史相呼应,梁启超对清代思想界的蜕变作了一个总的概括:“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按照这一框架,《清代学术概论》将清代前半期考证学或考据学的发展,视为第一步与第二步之解放,而将经今文学的兴起视为第三步、第四步之解放。叙述前两步之解放,较多利用了前人研究成果,而叙述第三步、第四步之解放,特别是叙述康有为作为中心带领梁启超一道推动经今文学运动的历史时,则几乎全部为梁启超所独创。
由于将清代二百多年考证学与经今文学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梁启超在叙述考证学与今文学的众多学人所取得的成就时,强调就是因为这些学人具有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学人同样的“科学的研究精神”,顾炎武以来许多学者所追求的经世致用,以及乾嘉汉学家经常提及的“实事求是”,都体现了这种精神。而在“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时,梁启超则反复说明正是因为没有始终坚持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
我以为,这一部著作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梁启超以科学的研究精神,对康有为和他本人所推动的经今文学运动的是非得失做了较为系统的叙述和有相当深度的检讨。我以为,他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有力地提升了《清代学术概论》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
康有为在晚清经今文学运动中的地位,梁启超给他的定位是“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康有为严划经古今文分野,以为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都是刘歆所伪造。于是正统派所尊崇所仰赖的学术依据,诸如许慎、郑玄等东汉古文学术,在康有为笔下皆成了伪史成了伪书。梁启超认为,由此,康有为将以复古求革新的文艺启蒙运动发挥到了极致,绕开东汉,回到西汉,既宗奉董仲舒张扬的《公羊》学,又从董仲舒的启示倡孔子改制,以为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无不以托古改制为基本手法。这是对乾嘉汉学正统派的颠覆,是对庄存与等常州学派以及廖平之学的张扬,一瞬间确实惊世骇俗,但正如梁启超所说,这一套学说,也未能摆脱“中国思想之痼疾”,即“好为依傍”与“名实混淆”。梁启超很直白地指出,这和康有为本人有密切关系:“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尤其是欲仿效欧洲宗教改革,图谋在中国建立孔教,完全脱离中国实际。这完全违背了“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的科学精神。梁启超回顾自己早年曾协助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检讨自己“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并明确宣布:“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屡起而驳康之建孔教、祀天配孔诸义。应当说,梁启超在这里所进行的自我批判和对乃师康有为的批判,方才是文艺复兴精神的真正体现。
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第三颗硕果,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本书初版于1921 年,后曾多次重版,并被译为英、法、日等十多种文字。一百年来,对这一部著作,肯定者,否定者,称许者,驳斥者,诠释者,引申者,过百盈千。所以,对于本书,无需多费口舌,加以介绍。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就是梁漱溟介入东西方文化论战时,知识基础和其他学人有着很大差异。1916 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研究佛学的成果《究元决疑论》,引起蔡元培的注意,被聘为北京大学专讲印度哲学的特约讲师。所以,他对印度文化有较多心得。他又出身儒林世家,父亲梁济1918 年殉清自尽,儒家文化传统极为强烈的影响力更深深震撼了梁漱溟。因此,他能够跳出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模式,通过西方、中国、印度这三大文明的比较,对这三种文化做出迥异于他人的新的解读。
梁漱溟以“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为题做了一个系列讲演。他看到,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其实形成于彼此非常不同的环境,有着彼此非常不同的人生路向,形成了非常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追求。他认为,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人们单纯地认知到我在,他们所建立的是一个“小我”,是与物相对立的我;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人们所建立的是“大我”,不是“分别我执”的我,而是“俱生我执”的我,不关注物之间的分别,追求的是人与物交融
为一体;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是“我”与“物”的完全消弭。这三种不同的生活,决定了这三种文化不同的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梁漱溟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分析和概括,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片面性,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掩盖他视野的开阔和观察的深刻。他所说的三种文化,实际上是三种文明,这些文明各有自己产生与生长的路径,各有自己的是非得失。他力主每一种文明都要善于吸取其他文明之所长,补自己文明之所短,但都不能丢掉自身的主体地位。这也许就是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选自《典藏1921》导读)